艾博年将治理置于观景之上——但在零和政治时代,这就足够了吗?

周五,我打电话给3AW,标志着资深广播员尼尔·米切尔的最后一次轮班。在最后一次与总理一起外出时,墨尔本的健谈国王拒绝多愁善感;米切尔把他的客人推来推去。
人们的狂热程度上升到听众可能会错过首相说一些非常有趣的话的程度。“为什么公众会反对你?”米切尔问道。艾博年说,民意调查来了又去,但首相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中期,“而不仅仅是日常政治,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最终将无法提供我们需要的那种政府”。
乍一看,艾博年的观察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政客在面对电台主持人像打小丑一样痛打他们时抛出的谈话要点——像是排练过的,是死记硬背的。
但这位首相试图分享一种洞见。他的意思是:我正试图打破自2009年左右以来困扰澳大利亚政治的一种模式。
我在努力治理国家,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至少在理论上,这一雄心应该会赢得首相的喝彩。如果你在街上拦住任何选民,问他们——首相应该优先考虑什么,是赢得政治胜利还是执政——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选民会说,请他妈的执政吧。选民们在2022年5月投票反对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很多人发自内心地反对,因为他把舞台和表演放在首位,以至于澳大利亚人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里。很难分辨什么是真实的。
注册澳大利亚卫报免费的上午和下午的电子邮件时事通讯,获取每日新闻综述
艾博年以反莫里森的身份获胜。他的口头禅是停止表演,开始行动。在因为不是莫里森而获胜后,艾博年计划通过塑造有序政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乔·拜登(Joe Biden)在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同理心、对制度的尊重、有序的政策议程被视为立法机构混乱的解药,以及白宫里一头愤怒的公牛。这些都是重要的实验,利害攸关。
艾博年并没有完美地执行自己的战略。球有时会掉下来。当危机(无论是人为的还是真实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时,政府可能会显得手足无措。随着夏天的临近,这群人看起来很疲惫,因为政府绝对是无情的。它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捻胡子就不那么麻烦了。
近几个月来,艾博年在对外宣传他的战略时,比在国内更有效。政府的大部分国内议程都是由个别部长单独完成的,他们低着头,在自己的地盘上无所事事。政府仍在过渡阶段,第一步,即前18个月立法选举承诺,第二步,即规划未来。这种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定义真空,正发生在生活成本危机的顶峰。
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陈述:在政治中,真空会让你变得脆弱,尤其是当选民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意时。
但艾博年告诉了米切尔真相。他优先考虑的是事情的本质,而不是外表,尽管这是一条更难走的路。这届政府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上一届政府不同,这让我感到震惊。莫里森是一位指挥型总理;内阁几乎无关紧要。艾博年的业务是分散的。部长们负责管理投资组合和政策议程;工作以小组形式在橱柜中完成。讨论可能会很激烈,但到目前为止,它们都是建设性的,只有最少的博弈。
我在政府工作了近30年。有几次,我对整个机构的健康状况深感担忧,尤其是在这十年的领导人政变和伴随而来的零和政治期间。从我的角度来看,一个专注于治理的政府的回归——处理实质性的事情,有时不够迅速或不够优雅,但仍在努力,试图做一些好事,而不是痴迷于自相残杀的清算、争斗和可怕的光学——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
很明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选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我们跟踪民意调查,就会发现,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表现得稳扎稳打,表现得实质性——同时拒绝破坏性、故作姿态、夸夸其谈——对政府奏效了。
但这一有利周期已经逆转。在《卫报》上,艾博年的选民支持率为负值,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在距离选举如此遥远的时候,关注两党倾向的措施就像咨询占星术一样有价值——但根据记录,现在这一比例接近50%。
我认为拜登的民调更糟。拜登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这让一些美国记者摸不着头脑。《名利场》(Vanity Fair)的特约记者Molly Jong Fast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认为“无聊”(指拜登)无法抵挡“特朗普式的混乱”。她推测,拜登政府的“超级大国,在为美国人民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又能在雷达下躲闪的能力,可能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阻碍了政府获得应有的荣誉”。
汤姆·尼科尔斯在大西洋上更进一步。他本周推测,能力实际上可能会让拜登在下次选举中失利,因为美国已进入“后政策时代”,选民对执政的具体细节缺乏兴趣。现在人们消费政治就像看真人秀或体育节目一样。“他们想支持英雄和高跟鞋;他们想要感受到强烈的情绪,尤其是愤怒;他们希望自己的选票能表达一种个人认同感……拜登无法满足这些愿望。这是他的功劳,但这在政治上扼杀了他。”
在美国,一切都更加紧张,也更加破碎。
但我们在这里确实看到了类似的现象,因为达顿和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澳大利亚人很愤怒。达顿也是。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挑战了澳大利亚人的集体慷慨,并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这些条件很适合达顿,他是一位威权民粹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地方。相比之下,艾博年是一位进步的国际主义者,本周他沉思着说,如果澳大利亚有更多的友善,它会变得更好。
正如艾博年以反莫里森的姿态击败莫里森一样,达顿现在正试图以反艾博年的姿态击败艾博年(这位自由党领袖本周曾大胆宣称,他曾在一个任期内击败艾博年)。正如达顿与时代精神之间存在一致性一样,达顿的两极分化政治与追求参与而非启蒙的社会和主流媒体机构之间也存在一致性。在契约经济中,纯粹政治的脉动是重要的。治理——一场增量游戏?其实不然。
现在的媒体生态系统就是要让人们有感觉;这就涉及到尼科尔斯在大西洋所提出的文化观点。这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区域。这不是一个解释或细微差别的区域。内容需要被观看和阅读,而被观看和阅读的内容主要是让人产生感觉的材料,而不是深入思考的材料。
与此相关的是一种严峻的决定论。本周的一个例子:我敢保证,关于部长们是否应该或不应该将达顿列为儿童性犯罪者的保护者(就像本周议会讨价还价期间发生的那样)的文章、言论和观点,比有关高等法院关于无限期拘留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的技术细节和含义的讨论要多。
达顿表示,对他的指控“与事实完全相反”。“确保妇女和儿童的安全是我一生的激情之一,我对此感到非常真诚和深刻,”他说,并要求道歉。
我把这些都拆开是为了说明一点。我们记者在分析什么在政治中起作用,什么在政治中不起作用时,可能太可爱了一半。因为历史的初稿是我们写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挤出视野,坐在廉价的座位上大喊:“看看那些白痴”。
最好是诚实。如果在全国的注意力范围内,“无聊”无法抵挡特朗普式的混乱(借用《名利场》的框架),那么我们——以及现在决定信息流动的激励机制——就是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试图治理好政府不能与壮观、轰动、道德恐慌和人为制造的分裂竞争——如果现在游戏结束了——那么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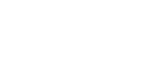
发表评论